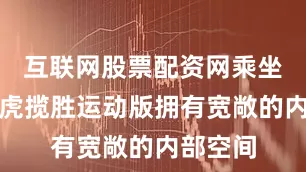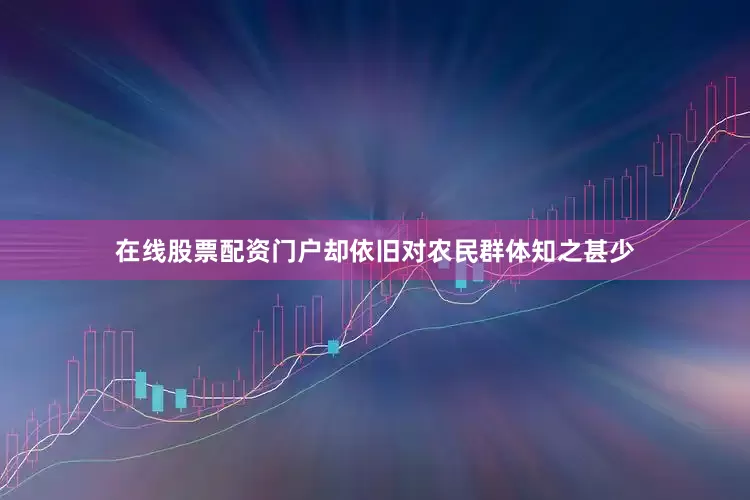
梁漱溟,堪称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璀璨明珠,同时亦是一位名噪一时的国际知名社会活动家。1950年1月,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人的盛情邀请下,他抵达了首都北京,光荣地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委员。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参加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之际,不幸遭遇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这一事件之后,他的地位从毛泽东的座上宾转变为“反面教材”,同时也预示着与毛泽东之间长达数十年的交往即将走到尽头。
这场争议的整个进程,先后展开于1953年9月8日至18日,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会的扩大会议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相继召开。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漱溟,亦获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9月8日,我国国务院总理同时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在提前举行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专题报告。
9日清晨,各小组如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随着小组召集人章伯钧先生观点的阐述,梁漱溟先生便就《人民日报》增设读者来信专栏的举措发表了个人感悟。他感慨而言:
此举不仅体现了民众对公共事务的深切关注,更凸显了党和政府始终倾听民声、解决问题的坚定决心。这种精神,在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理应得到一以贯之的传承。唯有始终坚持民主原则,广泛吸纳各方意见,才能将建国事业转化为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从而显著增强其成效。
“当然可以!我会在大会上发言。”

年轻时的梁漱溟
回到家后,梁漱溟心中想道,鉴于当前党领导层的负责人特命我在大会之上发表演讲,自当畅所欲言,贡献一番有益于党的领导之言论。他据此认真准备。
10日的会议发言异常激烈,梁漱溟未能如愿登上讲台。在会议的间歇时段,他致信周总理,提及在京城,他有机会发表意见的场合相对较多,因此恳切地请求周总理优先考虑外地代表的发言机会。至于他自己准备的发言内容,他建议以书面形式提交。周总理的回信中,他回应称无需担忧会议时间的安排,并表示可以适当延长会议日程,并诚挚地邀请他在次日登上大会的讲台,发表演讲。
在11日的会议上,梁漱溟发表了其观点。正是这番言论,激起了毛泽东对他的尖锐批评。
鉴于回顾的必要性,且为了论述的便利,不妨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一番细致的摘录。
梁漱溟说:
“接连数日,我倾听了多份报告,得知我国已踏入计划建设的全新征程,众人心潮澎湃,无不为之鼓舞。在此,我亦借此契机,以一位政协成员的身份和自身的过往经验,提出几点个人见解。”
往昔,我怀抱在中国掀起一番宏伟建国运动的壮志。四十年前,我投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激流之中,当时我深知政治变革的必要,但对国家建设的蓝图,却一片茫然。岁月如梭,数十载过去,我始终怀抱国家建设的梦想,虽未曾听闻新民主主义的理念,但我的理想与目标,实则与之相契合。
考虑到国家发展宏图在各层面均需实现协同与和谐,我推测,在政府向我们阐释建设重工业与改造私营工商业两项主要任务的同时,对于轻工业、交通运输等其他领域的发展亦应有详尽规划,并期望能够明确告知。这便是首项考量。
鉴于建国运动的推进离不开广泛的动员和深入的群众依靠,以达成既定的目标,这不禁让我对群众工作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加速工业建设的征途中,我坚信,只要得到工会的坚强后盾,我们便能够有效应对各种挑战。至于私营工商业的改革,则得益于店员工会、工商联以及民主建国会的积极参与;而在农业发展的广阔天地里,农会或许也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土地改革的关键阶段,农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随着改革的圆满落幕,其影响力似乎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那么,目前,我们不得不倚重于乡村的党政干部。然而,据我所知,这些乡村干部的行事风格,常常呈现出一种强制与指令的倾向,且在素质和能力方面似乎普遍存在不足。依循我之愿景,对乡村民众而言,必须大幅提升教育资源的投入,单纯依靠政令下达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我期望政府能够给予高度重视,并作出更加细致周全的规划。此乃第二要务。
第三点,我愿着重指出的是农民问题,亦或称之为乡村问题。在过去的将近三十年革命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民作为坚实的依靠,以乡村作为稳固的根据地。然而,随着我们踏入城市,工作重点逐步向城市转移,那些从农民阶层中涌现出的干部也陆续投身城市工作,这导致乡村地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空心化。尤其是近几年来,都市中的劳动者生活水平迅猛上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乡村的农夫生活依然艰辛。因此,大批乡村居民纷纷涌入城市,尤其是北京,以期寻求更加优越的生活条件。然而,城市的空间有限,不得不将这些外来者拒之门外,这一矛盾现象愈发显著。有人将这种现象比喻为,如今工人的生活宛如置身云端,而农民的生活却仿佛深陷谷底,两者之间存在着“九天九地”的巨大鸿沟。这话需关注。进城后,是否对他们产生了嫌弃?政府应关注此问题。
梁漱溟的观点一经提出,现场竟无一人提出反对意见,反而有不少人纷纷响应,表示对其观点的赞同。

梁漱溟与张澜、史良等友好
次日,即9月12日,政协常委的会议得以顺利转型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彭德怀就抗美援朝的形势进行了详尽汇报后,毛泽东即兴发表讲话。他情绪高涨地表示,部分人士对我国的发展总体方针持有异议,他们指出农民生活艰辛,呼吁给予更多关注。这或许正是儒家思想中所强调的施行仁政的生动写照。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仁政亦有大小之别。关怀农民虽是仁政中的小节,但推动重工业的进步、抵御外敌侵略则是仁政中的大业。毛加重语气道:竟有人在专业人士面前妄自菲薄,仿佛我党数十载如一日地投身农民运动,却依旧对农民群体知之甚少。此言何其荒谬!我们现行政权之根基,工人与农民的根本利益休戚与共,这股力量坚如磐石,不容分割,不容亵渎!
毛泽东此言虽未点明梁漱溟之姓字,但细心揣摩者只需一瞥,便能洞悉其言外之意,所指分明便是梁漱溟。此番话随即引起了梁漱溟的高度关注。
此刻,梁漱溟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意外的震撼,同时,一股难以平复的愤懑之情亦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他反问自己,何曾有过对总路线的任何异议?他始终坚定地拥护总路线。他并非意在削弱工农联盟,而是期望其基础更加牢固和稳固。于是,他急需为自己正名,并力图揭示事实真相。在会议中,他试图给毛泽东写信说明情况,然而信还未完成,会议便急促地落幕了。
回府后,他继续写信。本函旨在明确指出,本人所发表的意见绝无任何反对总路线、损害工农联盟之意,实则源于对国家福祉的深切关注。恳请主席能够在大会上撤销相关言论,以便消除对我可能造成的误解。

1938年1月,毛主席在延安盛情款待了莅临拜访的梁漱溟先生。
9月13日,梁漱溟亲赴会场,将自撰的信件亲手呈递至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随即安排于同日夜晚与之会面。遗憾的是,因时间紧迫,这场夜谈未能充分展开,彼此间的误会依旧未得化解。梁漱溟深感失望,却并未因此放弃。他决心在大会上再度阐明己见,以期获得与会人士的公正评议。
16日9月,梁漱溟得以在大会中发表其演说。他依次梳理了9日与11日的讲话要点,并多次重申,自己绝无反对总路线的意图。然而,当天,依旧没有人对梁漱溟提出任何批评。
9月17日,“纵然你未曾亲自动手杀人,却以笔为剑,刺向人心。”“尽管众人将你誉为良善之辈,我却直言你不过是一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即便下一届政协有意推举你,也仅仅是因为你擅长迷惑他人,使得一些人心甘情愿地被你所蒙蔽。”“若你明确地反对总路线,主张重视农业,纵然你的观点可能显得不够明智,但出于一片善意,尚可得到宽恕;而你若暗中反对,实则心怀恶意,这种行径却是无法宽恕的。”
此中央领导人的见解让梁漱溟内心波澜起伏,他深刻地感受到,因言语不慎而引发的误解已日益加剧。在他那执拗个性的驱使下,他毅然决然,不顾一切地强烈要求现场即席发言,以正本清源。
梁漱溟9月18日会上发言。
在昨日的会议中,中共领导人的讲话让我感到出乎意料。特别是主席的言辞显得异常严肃,明确指出我的初衷存有恶意。中共领导人回顾历史,力图证明我始终保持着反动立场。这无疑加剧了我阐述历史真实性的难度。然而,我与中共在解放前存在的异同,并非寥寥数语即可阐明,因此,我迫切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详尽的解释。
我恳切地提出一个基本诉求:请允许我有足够的时间发表意见。在昨天的会议中,尽管我的观点已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但若在今天未能给予我充分的发言时间,这无疑显得有些不公。我衷心期望领导党以及在座的非党同仁能够审慎考量,并赐予我展示自我观点的机遇。同时,我也坦率地表达,期待对领导党进行一次考验。此刻,我想要探询毛主席是否具有那样的胸襟,即在聆听我详细说明事件始末之后,能够告诉我,是我误解了梁漱溟的本意,他并无恶意。这正是我对毛主席所期待的高尚雅量。

毛泽东说,我无法展现你所期望的气度。
梁漱溟紧接着说,尊贵的主席大人,若您能够展现如此博大的胸怀,我必将由衷地敬佩您;而若您未能体现出这份宽厚的气度,我心中的敬意恐怕也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消散。
毛泽东回答说,我抱持着一份宽厚的胸怀,坚信您作为政协委员的角色仍有其延续的价值。维持您的政协委员身份,不仅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更是旨在让您得以持续担当此重任,进而发挥您作为生动教材的典范作用。
此时此刻,梁漱溟难以遏制心中激荡的情绪,言谈间流露出一种直率与坦率的鲜明特征。那是另一回事。
毛泽东生气地说,那是你说的。
梁漱溟接着又说,我党始终坚持并积极实践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今日,我愿亲自尝试,以检验您的这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行为,究竟是否真诚,抑或仅仅是表面文章。
毛泽东说,要么自我批评,要么受批评。
会场上呈现出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竟有人胆敢直面毛泽东展开交锋。忽然,听众中有人高声呼喊,声称不允许梁漱溟散布错误观点,坚决反对赋予反动分子任何民主权益,要求梁漱溟立刻退场!
毛泽东缓和地说:“梁先生,请您简要概述,请确保在十分钟之内完成。”
梁漱溟回答道:“面对繁多的论点亟待阐释,十分钟的时间显然捉襟见肘。在此,我诚挚地恳请主席能够赐予我一份公正的发言权。”
室内再次回荡起嘈杂之声,众多与会人员对梁漱溟的立场表达出强烈的不满,纷纷要求他即刻离场。毛泽东紧接着说道:
“若未充分听取他的意见,他便会觉得这是不公正的对待。但若给了他足够的时间,他可能会滔滔不绝地讲上数小时,而他面临的问题并非短时间内、数日或数月内就能解决的。需要指出的是,梁漱溟所遭遇的问题并不仅限于他个人,他的案例实际上揭示了其反动思想,有助于大家辨明是非。若不对梁漱溟的反动本质进行彻底的揭露和严厉的批判,是不可取的。因此,我提议再给他十分钟,让他简要地陈述观点,不知是否可行?”梁先生。
梁漱溟依然是时间紧,要求公平。的回答。
毛泽东最后说:梁先生,您提到我似乎缺少“雅量”,但同样,大家对您也有所保留,这并不能断定他们都不具备“雅量”。在您感到发言权被限制时,您批评了这种不公。但如果大家普遍不支持您的发言,那么何为真正的公平呢?在这种情形下,您有何见解可以分享?
梁漱溟面露不悦。“听主席决定。”
这时,建议通过投票的方式,以查明赞同他继续发言的票数是否超越了持反对意见者,进而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毛泽东率先举起手来,表达了对梁漱溟观点的支持,其他中共领导亦纷纷响应,举掌赞同。但与会者中的多数人却纷纷表达了自己的反对立场。面对这一局面,梁漱溟无奈之下,只得离开讲台,这才使得这场持续已久的僵局得以解开。

梁漱溟
不久,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提交了申请,决定暂时搁置参与各类会议与活动,以便能够更充裕地投身于阅读与学习之中,闭关进行自我反省。
在深刻自省的时刻,梁漱溟痛感自己犯下了严重过失,对于冒犯了这位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心中充满了深深的歉意。在亲朋好友与家人的慰藉与鼓励下,于9月22日,梁漱溟埋头案头,进行了认真而深刻的自我反省。
“对于错误产生的根源,我有何领悟?显然,它源自于我自身阶级观念的偏差。在解放之前,我对阶级理论持有质疑,这种疑虑根植于我的思想深处。随着共产党运用阶级理论建立了新中国,面对现实的洗礼,我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并曾怀着内疚之情尝试摆脱旧有的观念,转投无产阶级的怀抱。但这种转变只是短暂的闪念,我并未真正摆脱固有的思维束缚。”
比如我见证了劳动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激与无限崇敬,与此同时,我内心深处却深感自愧不如。这种差距源于我未能彻底摆脱旧有的观念束缚,无法在心理上与他们达到共鸣,共同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又比如在诸多场合,人们常常看到大家纷纷对共产党和毛主席表达敬意,而我往往只是默默鼓掌,以示我的赞同,却很少开口,积极参与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每当回忆起我国历经百年苦难、沉沦的岁月,直至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乾坤得以扭转,即便我千百次地呼唤“毛主席万岁”,仍觉得意犹未尽。然而,我身上遗留的旧习气和繁杂的杂念实在太多,竟然将这种情感当作“倔强精神”和“骨气”的象征,不禁有些沾沾自喜。须知,劳动人民对共产党的忠诚与热爱,并非仅仅表现为所谓的“倔强”与“骨气”。
正因我阶级立场存在偏差,对中国共产党认知有所偏误,才铸成9月18日那起荒唐的错误。我无视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深厚情感,在众目睽睽之下与毛主席争执对错,这无疑激起了众怒。因此,他人对我的批评与指责,实乃情理之中的回应。
回首1953年以前所度过的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我自诩投身于革命洪流,却最终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而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改良主义竟演变成了反动;加之我一贯秉持改良之道,自然而然地,我也成了反动势力的帮凶。因此,毛主席在会上对我进行批评,说我以笔为剑,无形中行凶杀人,当时我心中颇感不服。然而,直至后来我才豁然开朗,方才领悟到这句话所指的,是我那些年来反动言论在社会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主席再次指责我乃伪君子,当时我仅是淡然一笑,内心却并不认同。然而,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坚信,唯有舍弃私欲,拥抱革命英雄主义,方能铸就一颗纯洁无瑕的善良之心。至于我自身,若继续沉湎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浓雾之中,便难以做到纯真无欺,如此一来,便不免沦为伪君子的行列。
主席接言道:“我常被误信,确实有人受了我的误导。这无疑表明,尽管我并非十全十美,仍有他人对我抱以信任,给予我良善的评价。或许,是时候揭示这层光环背后的真实面目了。”
这些言辞充分彰显,自9月18日对毛泽东的不敬之举以来,梁漱溟始终秉持真诚,进行了深入的自我检视与反省,其中并无任何虚情假意。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公共场合对毛泽东表达异议,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获得与毛泽东单独会面和交流的机会。即便梁漱溟先生身为政协委员,其生活待遇依旧如故,且未受到任何组织的惩处。
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尊敬与深厚情感,始终如一,这份情感在心中悄然流淌。与此同时,毛泽东亦未曾忘却这位与自己同年出生、早在1918年便已结识的梁漱溟。
1972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同志的生日之际,梁漱溟先生特意将他自己精心编纂的著作《中国——理性之国》作为贺礼,敬献于毛先生面前。至1975年9月,毛先生在审阅某份文件时,提及了梁漱溟先生的名字,并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等成语,流露了对梁老先生的慰藉与深刻的理解。

三十余载光阴流转,踏入上世纪80年代的中叶,谈及那段往事,梁漱溟先生不禁感慨万千,语重心长地说道:
当时我态度颇为傲慢,言谈举止未曾顾及场合,让他陷入尴尬的境地。我深知,伤害他的感情实乃我之过,是我先行犯错。如今他已离世十年,我内心时常涌动着难以言表的孤独感。
文中流露出,梁漱溟虽给人以固执之态,实则内心充满了真性情。
西宁股票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